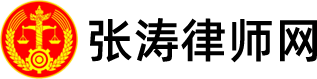例如:近日某男子名下持有多达16张银行卡,民警在哈市他的住处调查取证,现场搜出作案用手机、银行卡。案发后,公安成功破获一起“帮信”案件,抓获犯罪嫌疑人1人,涉案流水高达1000余万元。
站在辩护的立场,我们讨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,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,要求行为人“明知”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。
那么关于“明知”是如何认定的呢?
在任一要求主观明知的犯罪类型当中,均有着不小的争议。鉴于网络犯罪的隐蔽性、技术性、新颖性,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“明知”的判断,更是如此。“明知”,作为主观层面的问题,既要以表现于外的要素来证实,还要达到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的标准。否则,就会因为缺乏“明知”要件或认定“明知”证据不够充分,而不能被认定为犯罪。
人民检察院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,必须通过证据证实“明知”,通常有综合认定和司法推定两种方式。
第一,运用证据综合认定。
一般来讲,以被告人供述、同案犯供述、证人证言、电子证据等证据材料综合分析,查验被告人是否自认,有无他人指证,客观证据能否反映行为人的主观心态,全案证据结合起来是否能够排除被告人的自我辩解。
具体是行为人提供的技术、服务,自身行为是否具备合法性?是否接受他人指使、安排、指挥?有无酬劳?有无好处费?一对一还是一对多?对他人犯罪情况了解程度,根据常识或行业规范能否判断被帮助者是否从事违法行为,上游犯罪是否证成,对平台上充斥的非法信息、维权、投诉、举报如何处理等。
第二,以推定方法认定。
《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、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(以下简称《网络犯罪解释》)规定了七种推定明知的情形。以推定方法认定明知的情形,在一对多的场合下较为常见,比如,交易的行为有无异常情况,交易价格有无异常状况,交易地点、场所.提供服务的方式是不是隐蔽,有无销毁数据、通过虚假身份接触,是否逃避监管,有无处理举报等。行为人没有相反证据证实异常情况的,可以认定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。需要指出的是,认定“明知”虽然有迹可循,但主观心态认定是个经验问题,更是个复杂问题,不同的案件往往会呈现出不同的样态。这正是辩护人要重点关注的内容。因为,不论是通过证据认定“明知”还是推定“明知”,都须符合经验法则,符合证据认定标准。“明知”证据不足,无法认定行为人犯罪,检察院不起诉的案件并不少见。
实践中,行为人通常会将网络技术是否为犯罪分子所利用解释为,在公司,按部就班,拿固定工资,不了解公司犯罪情况,公司从事的是日常技术服务,不清楚他人是否从事犯罪”或是“公司服务的客户是不特定的,怎么能确定哪些客户是不是从事犯罪”再或“我和他们之间有明确的定价,价格适中,规范有序,也没有一起沟通过,怎么能了解他们是在犯罪”。
事实上,行为人主观上没有“明知”的辩解理由,基本可以概括为四种类型:
1、提供技术、服务的中立帮助行为。从自身经历或行业规范来看,对什么人会将技术或服务用来犯罪不知情。
2、面向客户的不特定性。行为人没有同客户有更多的交流,只是提供技术或搭建平台,以一般人的视角难以判断出客户从事的行为具有非法性。
3、提供的服务行为有明确的交易对价。双方交易的费用正常,交易行为符合市场要求,没有其他获利渠道。
4、公司内部正常履职,没有额外报酬。公司职员缺乏犯罪认识,欠缺认识犯罪所需的必要知识,没有认识到自身业务的非法性。
因此,面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,辩护人要充分把握“明知”认定规则,分析证据材料能否证实行为人的“明知”,审核被告人“辩解”是否难以反驳,将辩护做到有的放矢。